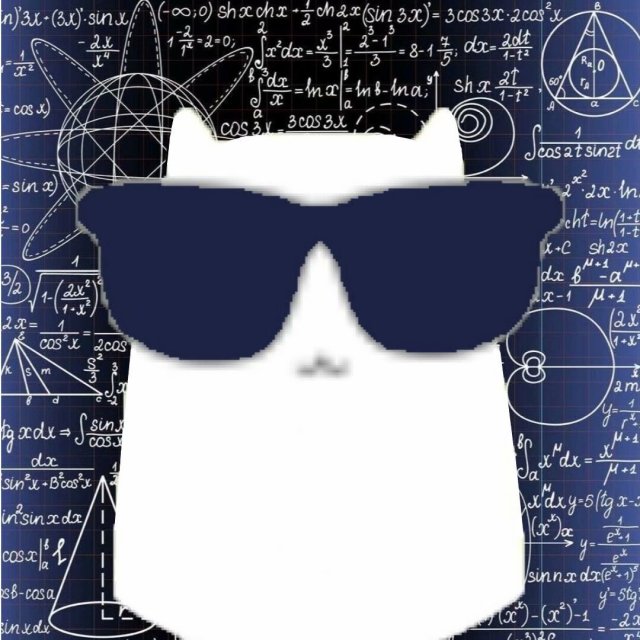我至此所阐述的内容,并不是为了承认这一不争的事实,即专以阶级利益为基准测试在权利受侵害时法感情的感受程度,借以证明所谓法感情依阶级、职业的不同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反映。恰恰相反,我想利用这一事实来证明远比其重要的真理,即试图正确评价这一命题,一切权利人通过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保护自己的精神的生存条件。因为上述三个阶级的例子中,在我们认为是各阶级的固有的生存条件的诸问题上,各阶级所显示出的高度反应。这一事实教导我们,法感情的反应与一般的感情不同并不取决于气质或性格这一个人的契机。它告诉我们与此同时存在社会的契机,即对该阶级的特别生存目的而言,该法律制度是不可缺的这一感情在起作用。据我看来,法感情对权利侵害反作用的能量是衡量感知法(即法和各种制度)对个人、阶级或国家自身和自己特定的生存目的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的比较确实的尺度。这对我而言,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对私法和公法都适合。各阶级对于构成其生存基础的一切制度表现的反映,同样在各国也分别作为对于被认为是特有生活原则具体化的诸制度的反应表现出来。其反应测量器以及测定国家对这些制度之重视程度的晴雨表,就是刑法。关于宽大和严苛,刑事立法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多样性,大部分可以从前已述及的生存条件这一观点找到根据。无论什么国家,一方面对威胁其固有生活原则的犯罪加以严厉处罚,同时对另外的犯罪,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采取宽大的方式处理。神政国家对读神和偶像崇拜打上了罪该万死的重罪的烙印,而对侵犯土地边界则视为简单的轻罪(摩西的法)。与此相反,农业国家则对后者科以毫不留情的刑罚,而对渎神罪则处以宽大的刑罚(古罗马法)。商业国家把伪造货币和其他伪造,军事国家把不服从、违反服役等,专制主义国家把大逆罪,共和国把君主复辟运动作为第一等之罪。而且不管哪类国家,对上述犯罪都利用与其他犯罪构成明显对照的严厉态度来处置。总之,国家和个人当感到固有的生存条件直接遭到威胁时,其法感情的反应也会更加强烈。
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条件给特定的法制度赋予极为崇高的意义,它提高法感情对侵害固有条件的反应,有时,相反地也消弱二者。仆人阶级不能象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具有名誉感情,因为他们的地位本身具有卑微性,只要其阶级本身甘于屈从,即使个人对此起来反抗也是徒劳的。对身处如此地位且不失虎虎生气的名誉心的人留下的道路,或是把自己的要求降至于他的同辈,否则只能放弃仆人职业本身。只有当这种感情普遍传布开来,才渴望对个人而言,不是将自己的力量消耗于无益的斗争中,而是同心协力地把自己的力量有效地投入于提高阶级的名誉水准。我在此谈到的不只是对名誉的主观感情,而是由社会其他阶级和立法给予的客观承认。在这方面,仆人阶级的地位在近50年间有显著改善。
至此我对名誉的阐述也适用于所有权。对所有权的感应力,即正确的所有感——我在此所说的所有感,不是营利欲,即对财富的无厌追求,而是所有权的男子汉般堂堂正正的感觉。作为这一所有权人典范的代表者,我例举过农民。农民捍卫所有物并不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有时呈不健全的状态或因一定事由而被削弱。常常有人这样说,即我的所有物与我的人格无任何关系。物对于我作为生计、营利、享乐的手段而发挥作用。但是,正如赚钱不是道德义务一样,为不足取之物而耗费金钱的时间,提起劳神费力的诉讼,同时也不能说是道德的义务。我在法律上主张财产的惟一动机,与财产的取得与使用之际规定我的一样,即我的自身利益——围绕所有权归属的诉讼是纯粹的利益问题。
依我看来,关于所有权的上述见解,只能认为是健全的所有感的堕落,而其原因只能认为在于对自然的所有关系的歪曲。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认为富裕和奢侈是恶的——要让我说,任何一方都不能威胁国民的法感觉——毋宁说,所说恶的是指营利的不道德性。所有权的历史源头和道德的正当性的根据是劳动。我所说的劳动并不是单指肉体的劳动也包括精神和技能的劳动。另外,我对劳动生产物不但承认其劳动者自身的权利,也要承认其继承人的权利。即我认为继承权是劳动原理的必然的归结。之所以如此,劳动者可随意放弃自己使用,无论在生前抑或死后,都不能禁止其让与他人,只要与劳动一刻不停地结合,所有权就不失其新鲜和健全。这一劳动的所有权一旦发现其得以不断产生、更新的源泉,所有权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就从根本上真相大白。但是,河流渐渐远离其源头,一旦到了不要任何气力,唾手可得的流域,水流便逐渐变浑浊,进而在投机和股票诈欺的泥沼中,其原有风貌消弥殆尽。在所有权的道德理念踪影皆无的地方,捍卫所有权的道德义务的感情无人问津也是理所当然的。为得到每日的面包而奔波忙碌的人们,谁都具有的活生生的所有感,在此却完全不被理解。更坏的结果,遗憾的是,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气氛和习惯逐渐传染到并非如此或几乎与此无缘的人们中、因投机而腰缠万贯的巨富的影响在穷人的小屋中也见得到。在另一种环境中,即使他具有与自身相符的经验,即认为收获缘于劳动,在这种氛围所具有的颓废的力量役使下,只会感到劳动是上天的惩罚——共产主义只能在所有权理念被冲刷殆尽的泥地上繁殖,而在这理念的源头看不到它的存在。经验告诉我们,统治阶级对所有权的看法,并不限于该阶级,也将向社会的其他阶级传播,但在农村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只要是在农村长期生活,与农民有些交往的人,纵使其环境和人际关系不助长之,他也会染上农民的所有感和节俭癖一类的东西。同样不分高下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处于完全相同的情形之下,若在农村则与农民一道成为节俭家,而在维也纳那样的大都会,则与百万富翁一道成为挥金如土者。人们只要不为标的物的价值所刺激而反抗,宁愿图安逸,而回避为主张权利而斗争。这种不坚定思想的原因何在呢?对我们而言,问题仅是认识这一思想,揭示其本来面目。阐明这一不坚定思想的实际的处世哲学,只能是胆小怕事的策略。从战场上逃脱的胆小鬼可使自己的生命免于象别人那样的牺牲,但这个胆小鬼为保全生命而牺牲了荣誉。其他人坚守不退怯的立场,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要保护自己和集体以免遭通常由胆小鬼的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假如大家均象胆小鬼那样考虑的话,将会是全军覆没的。完全相同的道理对因胆小怕事而放弃权利也适合。即使作为单个人的行为是无害的,但如果把它上升到行为的一般的处世观,法本身将遭到破坏。尽管如此,上文中的怯懦行为,乍看无害,就是因为法对不法的斗争尚未由于卑怯的行为而受到更大的妨碍。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斗争不但是由个人进行的,在发达国家,国家权力也大规模地参加这一斗争,积极追究处罚对个人权利、生命、人格和财产的所有重大侵害。警察和刑事审判官为权利主体承担了保护权利工作中的极其重要部分,而且对完全委诸个人追究的权利侵害,这一斗争从未中断过关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承袭胆小怕事者的计谋,而且胆小怕事者一旦争执标的物的价值超过了自己宁愿息事宁人的程度,就会投身于斗争者的行列。否则,可以想象不需要在背后支持权利人的警察和刑事司法,也可以让我们置身于古代罗马那样把对盗窃和强盗的追究完全听任于被害人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上述权利的放弃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将不言而喻。难道不只会是鼓励盗窃和强盗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间关系,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任何国家都是完全自立的,在协助其权利伸张之上不复有更高的权力。由争执标的物的物质价值来决定是否抵抗不法的处世观,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点只要读了我上文中的那个一平方英里土地的例子就会明白。
这种处世观无论我们在何处验明都无法得出权利的损坏和破灭以外的结果,假如在另外有利因素的促使下,例外地消除了不良结果,也不能认为它是正确的。在这种有利的状态下,这一处世观是如何地传播有害影响的,将留待后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