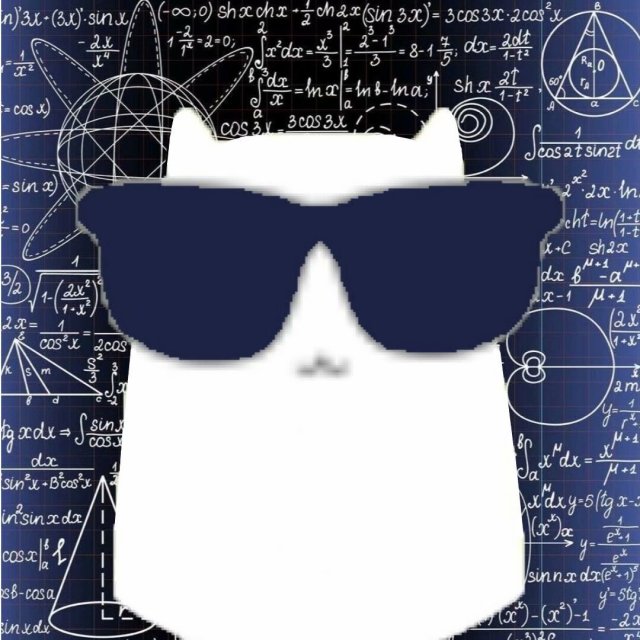关于这个问题在极低的发展阶段上的情况,我曾做过研究并已公布于世,现将结论在此加以简短概括。古代易于激动的法感情对于自己权利的任何侵害和反对,完全不顾对方是否清白和责任程度。从主观的不法角度来看,对没有责任的人也同有责任的人一样,要求赔偿。否认明白无误的债务(Nexum发生债务不履行时,债务人不经判决就处于隶属状态的拘束行为)和自己加于对方物上损害的人,败诉时须支付双倍,在所有权返还请求诉讼上,作为占有者取得孽息时,必须双倍赔偿。在本案诉讼中败诉时,还将失去诉讼赌金(供托金Sacramentum),原告败诉时也同样受罚。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要求别人的财产。原告所诉债务额若有一星半点不符,即使对此有充分理由,也将失去全部请求。
古罗马法的这些制度和原则多数为更新的法所继受,但新法独自的创造物吸取了完全别样的精神,其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过失这一尺度在一切私法关系上的确立和适用,将客观的不法与主观的不法严格地区分开来。前者伴随而来的是对有责任的对象单纯的回复原状,而后者伴随而来的是除此之外,还将处以罚金或名誉丧失。并且把这一处罚限定于正当的界限之内,这正是中期罗马法极为健全的思想之一。受托人不正当的否认或拒绝交出寄托物而犯有背信行为,受任人和监护人把信用上的地位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或以恶意怠于履行义务,对此用单纯的物上返还和损害赔偿就可免除责任,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罗马人首先为了满足被侵害的法感情,接着为了震慑想要作同样坏事的人而要求给这些人以处罚。在所适用的处罚之中,不名誉之罚居上位——此罚根据罗马情况是能够考虑到的处罚之中最重者之一。之所以如此,这种罚除招致社会性的部落制裁之外,伴随着政治权利的丧失即政治上死亡。当权利侵害带有特别的背信行为特征时,常被课以此种处罚。此外还有财产刑,其使用之频繁,现在无以类比。对因犯不当之事而引起诉讼和主动提起诉讼的充分准备了这种威吓手段,即它从争执标的物的价值的几成起算(1/10、l/5、1/4、1/3),最后可达数倍。在不能以其他方法回击对方反抗的情况下将至无限额,即可以提高到原告通过宣誓认为充分的数额。特别是存在下面两种诉讼制度,对被告而言或是在没有招致更不利的结果之前,想出大胆的计谋,或是被宣告为有故意违反法律之责,结果使自己面临被处罚的危险,两者必择其一。法务官(Prator)的禁止命令和专决诉权(actiones arbitrariae)即是。不尊从政务官(magistat)或法官给被告下达的命令,这将成为一种拒绝服从、反抗,这以后不只是原告的权利,同时法律以其代表者的权威兴师问罪,无视这一切将由罚金补偿.这罚金归于原告。
这些处罚的目的与刑法上的处罚目的大抵相同,即首先从不构成犯罪概念的侵害中保护个人生活的利益,这一纯粹实际的目的。其次给与受侵害的法感情以满足,通过法恢复被蔑视了的权威的名誉,这一伦理上的目的。然而,此时的金钱不是自己的目的,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据我所见,这个问题在中期罗马法上的表现是典型的,从古代法把客观的不法与主观的不法不加区别,一并处理的极端,从现代法民事诉讼上把主观的不法降格同客观的不法来处理这一正相反的极端,不偏不倚,相互严格区分两种类型的不法,并且在主观的不法范围内以纤细的理解力区别有关侵害的形式、种类、程度等一切细微含义,通过掌握这一技术,充分满足健全法感情的正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