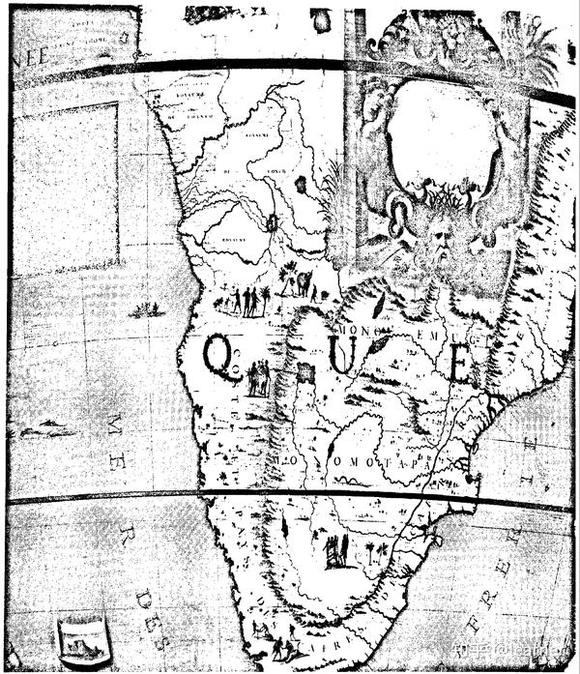|
41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38

對如此地理劃分的表現亦是符號挪用的領域。在西方圖像志中,歐洲頭戴象徵城市文明和軍事力量的塔形頭飾(tower)[8],身着代表帝國的紫色奇異斗篷,裝點有權杖和聖球(orb)這些帝王符號。伴隨她的公牛是指朱庇特化身為牛劫奪歐羅巴,將她從雅典帶到克里特島(Europa)的傳說,那是一個為了歐洲人文主義的文化建構工程被回憶起並被鋪展成為歷史依據的故事。[9]大陸的顏色,每塊大陸最高點與最低點的確定,它們的地理中心、對跖點和每塊大陸最長的河只是地球儀和世界地圖上銘寫下的許多知識建構中的寥寥幾個。同自然現象、聖人事跡、歷史事件的真實發生點一道,它們表達並建構了詩性地理,在全球表麵塑造意義。尼羅河及其非洲河源從古代世界延續至蒸汽鐵路時代和電報時代的歷史,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8]塔形頭飾(tower)是英國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統治時期的一種很高的頭飾,呈塔形,由硬紙板、平紋細布、網眼織物和絲帶製成。——譯者注,參考了牛津詞典相關條目
[9]約翰·黑爾(John
Hale),《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倫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1993年,第 7-11頁;米高·J. 赫弗南(Michael J.
Heffernan),《歐洲的含義:地理與地緣政治》(The Meaning of Europ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倫敦:阿諾德出版社(Arnold),1995年,第9-48頁。
|
 |
42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38

在全球地理分佈中尋找規律和形式對稱的努力,持續顯露出匹配形而上學秩序和全球地理秩序的宇宙地理學渴望。中世紀三大陸地盤(terrestrial
disk)式對地球的表現形式、早期現代地球儀上人們長期想像存在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和對北方海上航線能夠平衡環南極航行的堅定信念,說明全球對稱性對人們想像力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歷史。追求全球對稱的理性主義理論提綱迅速關注到了歐洲航海家所揭示的不斷變化的海陸模式:奧特柳斯力圖使非洲海岸線與南美洲海岸線相合,而在《新工具》中弗朗西斯·培根是最先幾個注意到它們作為有地峽、從赤道到南端的岬角不斷縮窄的大陸的相似性,認為「這不能說是純出偶然的」[10][11]。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將海洋陸地的對跖不對稱性整理為理論,而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數學家阿列克謝·舒利加(Alexei
Shulga)聲稱八面體有助披露大陸地塊和深海海溝的相似性與對稱性,相同的模式沿着赤道每過九十度就重複出現。[12]對地球表面模式的基本秩序的主張,不僅是被觀測科學驅逐出去的、令人發笑的迷思和幻想。它們也顯示出以秩序之夢制御地理多樣性的形而上學渴望——從而經常也包括文化多樣性。它們在塑造人類身份和行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10]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轉引自詹姆斯·羅姆(James Romm),《大陸漂移說的一個先驅》(A New Forerunner for
Continental Drift),載《自然》(Nature)總第367期,1994年,第407-408頁。
[11]譯文引自培根:《新工具》,許寶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67-177頁。——譯者注
[12]維克托·N. 紹爾波(Victor N.Sholpo),《地球空間的和諧性》(The Harmony of Global Space),載《塗鴉地理學第一輯》(Geograffity 1),1993年,第6-15頁。
|
 |
43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38

和在西方全球想像演進中的實際地點同樣重要的,是已知與未知空間之間的疆界。平面地圖上已知的區域可以一直延伸到描繪空間的邊緣,暗藏起於邊框之外還存在着什麼的問題;在地球儀上,「世界的盡頭」就不能被忽略了。地球儀在第一次環球航行那幾十年大行歐洲並非偶然。[13]實際上,地球表面的盡頭也是起點;心理上,無限隱含着與秩序消散一同發生的混亂。古代世界沒有留下明確的製造地球儀的證據;單是對球形大地的知識就使得劃分其已知空間的疆界成為必要。地球的盡頭超越了古希臘的人居世界(oikoumene),那個由氣候區和地中海一帶的海陸模式從理論上決定下來的地區(見圖2.3)。[14]從希臘羅馬時代地球的邊界就被畫出來區分人文和自然的其他部分、顯示帝國對自然和各個民族的支配權。
[13]見第4章、第5章。關於地理上的未知區域同心理上受到壓抑與恐懼的「他者」之間的關聯,見瑪麗·赫爾姆斯
(Mary Helms),《尤利西斯之帆:權力、知識和地理距離的人種學奧德賽》(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Knowledge,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8年。
[14]斯坦斯扎克(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第34-36頁。
|
 |
44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39


2.3
對亞里士多德的人居世界(ecumene)氣象模型的當代重構,來自讓-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亞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筆下的氣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爾馬丹出版社(L』Harmattan) |
 |
45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40

地球描繪方式的含義在相關文本和圖像中得到了擴展,無論是在其空間邊框之內還是之外。奧特柳斯的世界地圖題為《寰宇大觀》。將這幾個字置於在東西南北有人形「風頭」(wind
head)伴隨、祥雲托起的渦輪花飾(cartouche)內將這張圖像與羅馬帝國的修辭建立起了關係,正如同將1972年NASA地球照片命名為「地球太空船」與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文化流行的使命與孤獨意象相聯繫。在水陸組成的空間中,含義也能得到相似的擴展。比如,在十七世紀溫琴佐·科羅內利(Vincenzo
Coronelli)[15]的大地球儀中,詳盡的文本提供了只有在製作這個地球儀的特殊語境下才清晰易懂的、複雜的歷史學、人種學與寓言學註釋(見圖6.9)。[16]它們的重要性既體現在它們的存在與方位,又體現在它們所敘述的情況,前者暗示那塊地方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麼比文字上說得更重要。圖畫也承擔了相似的功能。在地球儀和地球投影圖上的海洋空間中不但畫上線性的波浪,而且畫上海魚、海洋哺乳動物和海怪在長久以來平常可見,它們許多都是寓言性質的。例如,在1570年朱利奧·薩努托(Giulio
Sanuto)[17]所畫的地球上,一個海怪從他所刻的提香(Titian)的《帕修斯和安德洛墨達》(Perseus and
Andromeda)移向南部海域,這是轉移到地球空間上的神話時刻。[18]地球儀和球體投影圖上複雜的符號註釋充當了日後圖像中被回想與挪用的知識和信仰殘餘,持續影響着地理想像。
[15]溫琴佐·科羅內利(1650.8.16-1718.12.9),是意大利方濟會修士、製圖家、出版商,尤以其地圖冊和地球儀聞名,生命大多數時光居住在威尼斯。——譯者注
[16]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地圖帝國:透過歷史看製圖學的理論方法》(L』empire des cartes: Approche théorique de
la cartographie à travers l』histoire),巴黎: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Albin
Michel),1992年,第229-231頁;另見下文第7章。
[17]朱利奧·薩努托(活躍於約1540-約1580),是威尼斯版畫家。——譯者注
[18]米高·伯里(Michael
Bury),《朱利奧·薩努托:一個十六世紀威尼斯版畫家》(Giulio Sanuto: A Venetian Engrav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愛丁堡:蘇格蘭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1990年。
|
 |
46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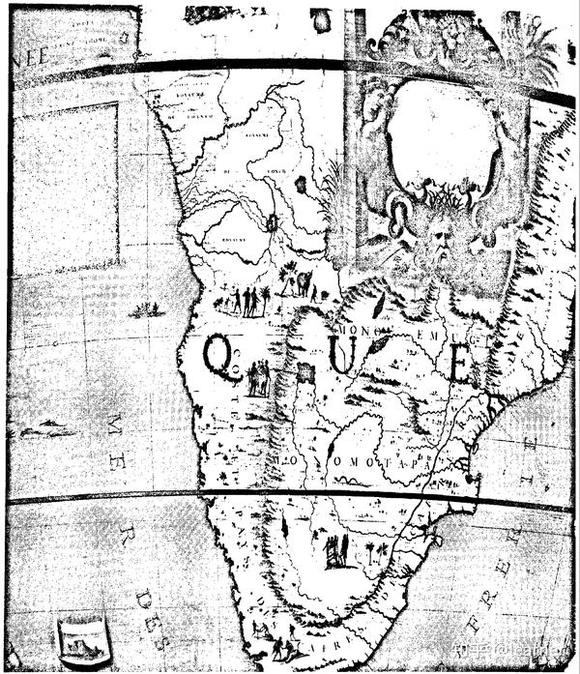
6.9 科羅內利為路易十四製作的地球儀細部,將尼羅河的源頭飾以插畫,1683年。圖片來源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 |
 |
47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41

全球、全球主義、全球化
|
 |
48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41

這些章節的圖像以不同的方式各具全球性(global)。[1]全球性(global)指的是一系列範圍持續擴展的環境、經濟、政治和文化進程。它的許多力量來源於這樣一種引人注目的觀念:地球,作為單一的空間,是由相互聯繫的生命系統與其表面組成,而在其表面上,現代科技系統、通信系統和金融系統不斷克服時空限制以達致彼此協調的同時性。就連認為全球進程不均等、破壞當地的這種負面評價,也在全球空間的權利平等和機會平等的意義上依賴了對全球主義的不可見允諾。濫砍亂伐、大氣污染或者沙漠化擾亂了自然世界,威脅了全球自然平衡,這種信念的增強既是依靠全球信息的即刻傳播,又是依靠上述這些人類活動自身。全球進程的話語影響,似乎恰恰是在長久以來在歐洲中心主義想像中居於人居世界(ecumene)邊緣的地區增強的。[2]因此,熱帶雨林、極地冰蓋、沙漠和深海在當代引發的種種聯想,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因於西方全球視覺形象和全球想像的歷史。
[1]哈利(Harley)與伍德沃德(Woodward)在《地圖學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一卷序言中指出,地圖學(cartography)一詞是十九世紀的發明。 [2]Ecumene,一作oikoumene,以下均指地球的宜居區域。 |
 |
49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41

全球化(globalization)賦予了當代不斷加速的全球主義進程一個社會經濟學和政治動力,甚至是目的(teleology)。經濟上,金融市場、商品市場和貿易市場的整合響應了極具流動性(hypermobile)、脫離對某一地點附着的資本的需求。這一進程在西方帝國的歷史中有其深厚根源,荷蘭東印度公司、哈得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3]等「全球」貿易團體是其現代形式的始作俑者。社會上,談論全球分工、全球生產、貨物和信息的全球營銷和全球消費,並將這些與在時空上保持在地性的生活過程進行對比,正變得越來越具有意義。各種政治現象,比如「世界」大戰(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國際宗教組織、人道主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具有全球外交影響力和軍事影響力的超級大國,甚至使南極洲擺脫相互衝突的領土主張的國際協定,都令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術語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意義非凡。文化上,全球尺度似乎越來越適於描述與解釋這種種現象:互聯網、電影院、視頻和流行音樂、新聞編排、快餐、飲食偏好、服裝選擇與個人時尚選擇、旅遊業,甚至還有科學操守與藝術操守(artistic
integrity)、人權與道德行為。[4]
[3]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於1670年註冊成立,是一家根據英國皇家特許狀進入哈德遜灣進行貿易的公司,在約兩百年間實際上控制了現加拿大中部地區。——譯者注
[4]關於歷史視角下的全球化,參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共3卷,倫敦:學院出版社( Academic
Press),1974-1988年;還有J. M. 布勞特(J. M. Blaut),《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史觀》(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紐約:吉爾福德出版社(Guilford),1993年。關於更多社會學角度觀點,參見米高·費瑟斯通(Michael
Featherstone)編,《全球文化:民族主義、全球化和現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倫敦:世哲出版社(Sage),1990年;及M. 奧爾布羅(M.
Albrow)和E. 金(E.King)編,《全球化、知識與社會》(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倫敦:世哲出版社(Sage),1990年。關於全球化的地緣政治機制,參見J. 阿格紐(J. Agnew)和S. 科布里奇(S.
Corbridge),《掌控空間:霸權、領土和國際政治經濟學》(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5年.關於全球化的文化地理學,參見多琳·馬西(Doreen
Massey),《一種全球性地域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載《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1991年六月號,24-29頁;以及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牛津:布萊克韋爾(Blackwell),1989年。
|
 |
50樓
令和野狗
2025-12-31 14:42

當代全球化至少部分導致了全球地理學的去中心化,這真是一條重要的見解。知識和影響力從中心區域生發,向地球邊緣涌流,但從中心區域出發想像全球,還不足以捕捉那發生在每條聯繫兩端的相互形塑,儘管這種形塑並不是均衡的。「網絡」和「根莖」這樣的空間比喻於是代替了取決於帝國和歐洲中心主義視域的「核心」與「邊緣」。然而,持續擴張的人口、對新消費品不斷增長的需求、有權有勢的精英為爭奪領土和地位的競爭,還有教義上的黨同伐異從大約1450年開始在500年間塑造了強而有力的歐洲中心的全球主義,這卻也是不爭的事實。[5]在歐洲伊比利亞半島邊緣同步進行的擴張,和對另類「中心」的重新構建,利用並重塑了歐洲古代全球帝國主義的記憶。[6]在歐洲擴張進程中逐漸發展的、全球和地球的圖像和印象,既塑造了全球化世界的實際狀況,也被這種實際狀況所塑造。當然,全球化永遠是部分、依具體情況而定的,永遠和更加在地的視角和經歷相持不下着。[7]因此,帝國城市的景觀——尤以羅馬最為顯著——揭示出,中心永遠需要得到建構,永遠需要得到在想像中的不斷再造,以此表達凱撒、教皇和帝國的全球空間性。
[5]布勞特(Blaut),《殖民者的世界模式》(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6]彼得·休姆(Peter
Hulme),《殖民遭遇:歐洲和加勒比海原住民,1492-1797年》(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86年;安東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歐洲對新世界的遭遇: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From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紐黑文(New Haven):耶魯大學出版社,1993年。
[7]德里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地理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牛津:布萊克韋爾(Blackwell),1994年;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牛津:布萊克韋爾(Blackwell),1996年.
|